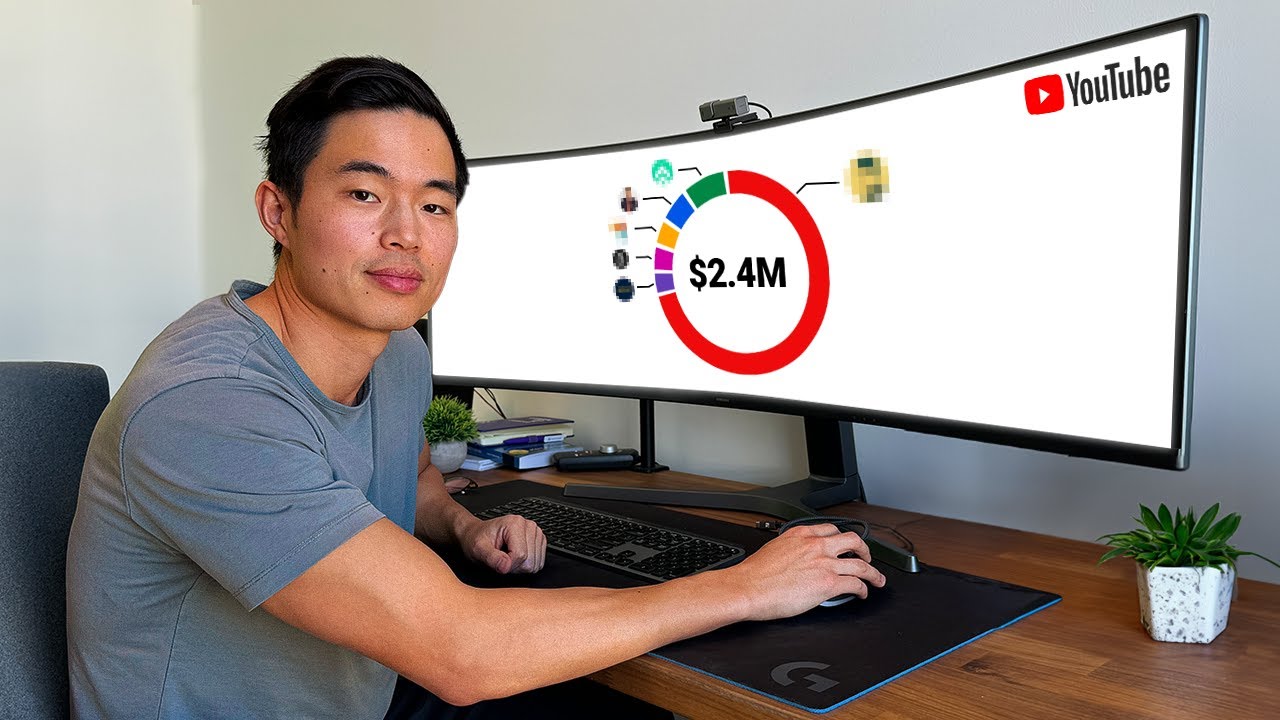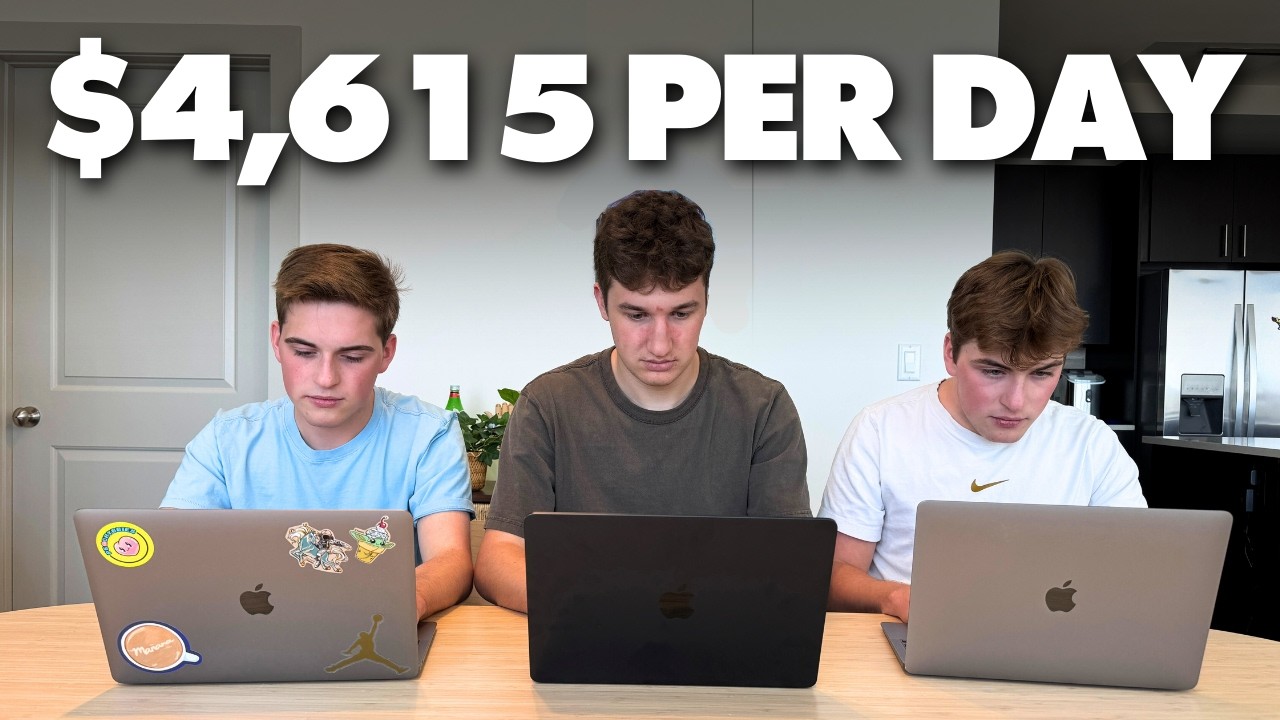00:43:19
全球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:增长失速、不平等加剧与大国博弈
全球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,财富分配不均日益严重,大国之间为争夺增长份额而采取的关税与保护主义政策,正共同构成当今世界经济的“新常态”。本文将深入剖析这一系列现象背后的根本动力与未来走向。
核心要点
- 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熄火:世界经济增长率已从1950年代的5%大幅下滑至2010年代的2.9%,未来预期更降至2.4%。
- 不平等是动荡的根源:新增财富的95%被顶端10%的人口获取,底层90%的人口仅分享5%,导致各国内部政治极端化。
- 增长的三驾马车全部失灵:资本投入因高利率受抑,劳动力因人口老龄化萎缩,生产率提升也遭遇技术瓶颈。
- “掠夺性增长”成为大国策略:中美等国试图通过关税、补贴等方式,从其他国家“掠夺”增长份额以弥补国内不足。
- 未来格局:单一超级大国主导的局面可能减弱,地区性强国和阵营化竞争将成为未来数十年的特征。
一、经济增长为何全球性失速?
许多人将当前的经济困境归咎于个别领导人的政策,但真正的根源在于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长期结构性下滑。全球经济增长率在1950年代曾高达5%,而到了2010年代,已降至2.9%。世界银行的最新展望更是预测,未来全球年均增长率仅为2.4%,近乎腰斩。
增长放缓的直接后果是各国内部矛盾激化。当“经济蛋糕”无法持续做大,而其中绝大部分又被极少数富人分走时,社会的不满情绪便会急剧升温。数据显示,全球新增财富的约95%流向了收入最高的10%群体,而剩下的90%人口只能分享5%。这种巨大的不平等是当前全球政治极端化、内部撕裂的根本原因。
二、三大增长动力全面熄火
经济学家通常认为,经济增长源于三大动力:资本投入、劳动力投入和生产率提升。不幸的是,目前这三架马车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阻力。
1. 资本投入:高利率时代的困境
2010年代,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平均仅为1.5%,而如今已飙升至4.4%以上。资本变得昂贵,企业融资成本大幅上升。对于沃尔玛(营业利润率2-3%)、亚马逊(约10%)或韩国企业(平均6-7%)而言,当无风险收益率都高达4.5%时,进行高风险投资的意愿自然大幅降低,导致投资萎缩,就业市场疲软。
2. 劳动力投入:人口断崖的挑战
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都面临着人口萎缩问题。法国的总和生育率约1.8,美国约1.6,但这主要依靠移民维持。其他欧洲国家多在1.3左右,日本为1.1,韩国更是低至0.76。总和生育率下降约20年后,生产性人口(15-64岁)开始减少,经济将遭受重创。日本1990年代后“失落的30年”及2010年代欧洲经济的停滞,其核心原因都是生产性人口的减少。
3. 生产率提升:技术革命的边际效益递减
许多人认为IT和AI时代生产率会持续提升,但事实可能相反。研究表明,当前生产率提升幅度远低于1940-50年代。电报的发明将越洋信息传递从14天缩短至10分钟,其带来的效率提升是革命性的。而智能手机相较于之前的PDA(个人数码助理),虽然更便捷,但属于渐进式改进,带来的额外生产率提升远不如前者。重大基础技术已被广泛应用,新的突破性技术所能带来的边际增益正在变小。
三、不平等的恶性循环:宽松货币政策的副作用
面对增长放缓,各国央行普遍采取宽松货币政策(印钞、量化宽松)。但这些新增货币并非直接分配给民众,而是通过商业银行体系进行分配。银行更愿意将资金借给信用好、有资产的富人,而非普通家庭或中小企业。
其结果是,每次危机都成为财富向上集中的加速器。在危机中,资产价格暴跌,富人们凭借其更容易获得的廉价信贷大量购入折价资产。数据显示,1990年,美国顶端1%群体的财富占20%,底层90%占45%。而到了2015年,顶端1%的财富份额历史性地超过了底层90%,这种情形上一次发生是在1920年代末——即“大萧条”的前夜。大萧条的本质是底层90%的资产缩水,购买力枯竭,而顶端1%的财富却持续膨胀,最终导致总需求崩溃。
四、大国博弈:从“共同增长”到“掠夺增长”
当国内政策工具(货币和财政政策)用尽仍无法有效刺激增长时,像中美这样的G2大国便开始利用其体量和影响力,试图从其他国家“掠夺”增长份额,其主要手段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和补贴战。
这一策略并非由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首创。在其上任前,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0.7%,之后逐渐降至7%、6%,乃至近年的3%左右(官方数据为5%)。为了维持增长和社会稳定,中国采取了大规模补贴本国出口产业的策略(例如,购买一台中国扫地机器人或电动汽车,其价格的30%可能来自政府补贴),旨在摧毁他国的制造业基础,将增长和就业机会“吸向”中国。
美国作为回应,特别是特朗普上台后,采取了更极端的关税政策进行反制,并且将矛头不仅对准中国,也对准了盟友,试图将所有人的增长都“抢回去”。全球贸易秩序从合作转向了零和博弈。
五、未来展望:混乱的“多极”世界与中国的挑战
特朗普的关税策略基于其2018-2019年的经验,当时中国通过货币贬值和加大补贴吸收了关税成本,美国通胀并未上升。但现在环境已变:中国债务高企(总债务/GDP从2008年的80%升至如今的320%),难再大规模补贴;全球通胀高企,各国也难以通过货币贬值来应对关税。特朗普的策略可能是一把伤己也伤人的“双刃剑”。
中国虽在制造业产出和AI等领域发展迅猛,但也面临巨大的人口结构挑战。其抚养比(每100名劳动人口需抚养的老人和儿童数)将在未来50年内从目前的40左右飙升至140,与美国(从60升至70)和韩国(更高)相比,形势极为严峻。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窗口内,在AI和机器人领域取得绝对优势,以克服劳动力短缺,否则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。然而,将全部资源押注于尖端科技,导致内需和房地产业等其他部门凋敝,可能引发巨大的社会不满和政治风险。
未来可能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超级霸权,而是进入一个美国领导力相对减弱、多个地区性强国(如土耳其、以色列、沙特、伊朗)崛起并相互竞争的“多极”时代,地区冲突和阵营化趋势可能会更加频繁。
结语:韩国的机遇与挑战
在全球大变局中,韩国因其独特的制造业能力和人均GDP水平,仍有其价值。美国在高端制造和 robotics 方面成本高昂,需要可靠的合作伙伴,韩国有望扮演这一角色。然而,这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在中美之间取得平衡。同时,全球性的经济增长放缓和财富分配不公同样在冲击韩国社会,如何避免内部政治极端化和社会撕裂,是比应对国际博弈更为紧迫的挑战。
全球经济的“地壳”正在剧烈变动,其深层动力源于增长、分配与权力的根本性转变。理解这些趋势,是思考个人、企业乃至国家未来出路的第一步。